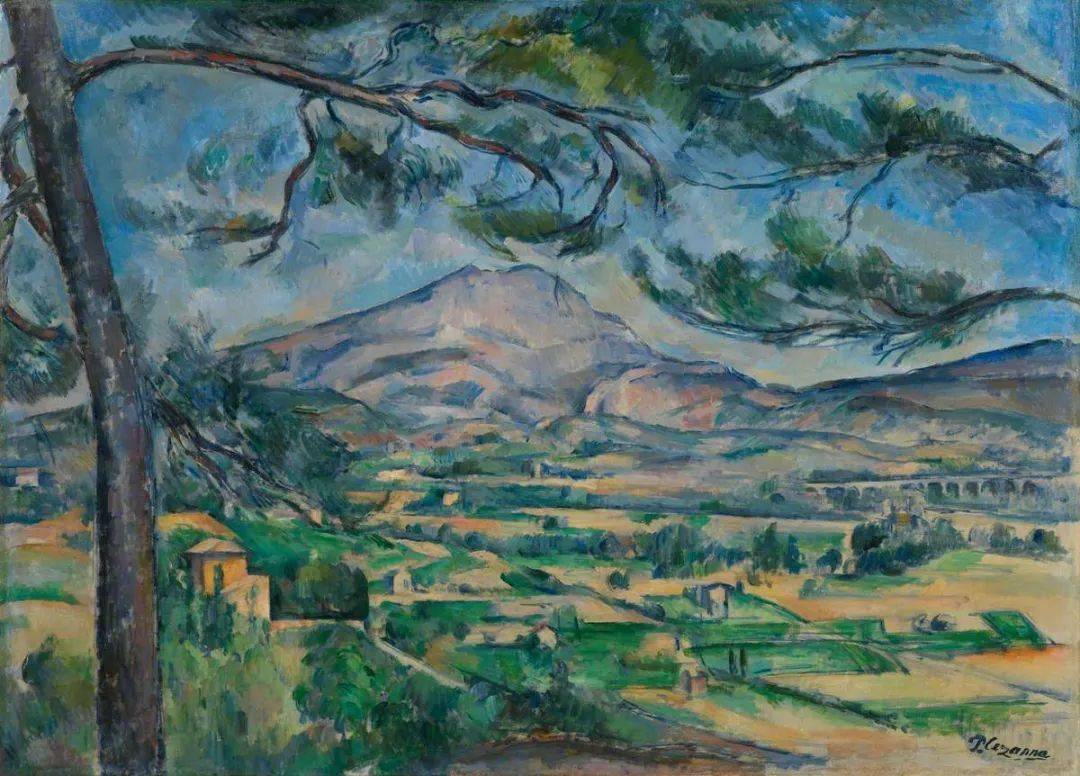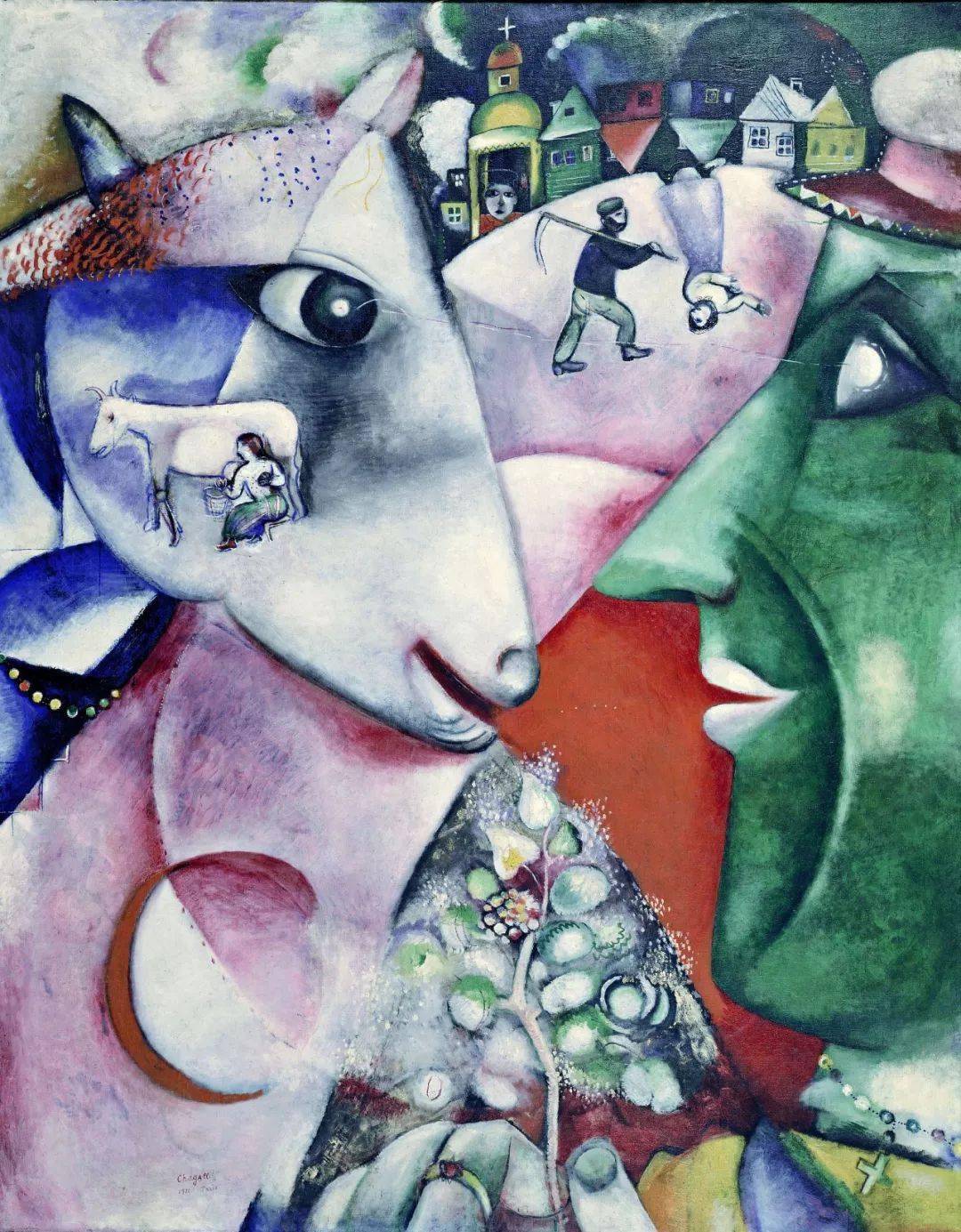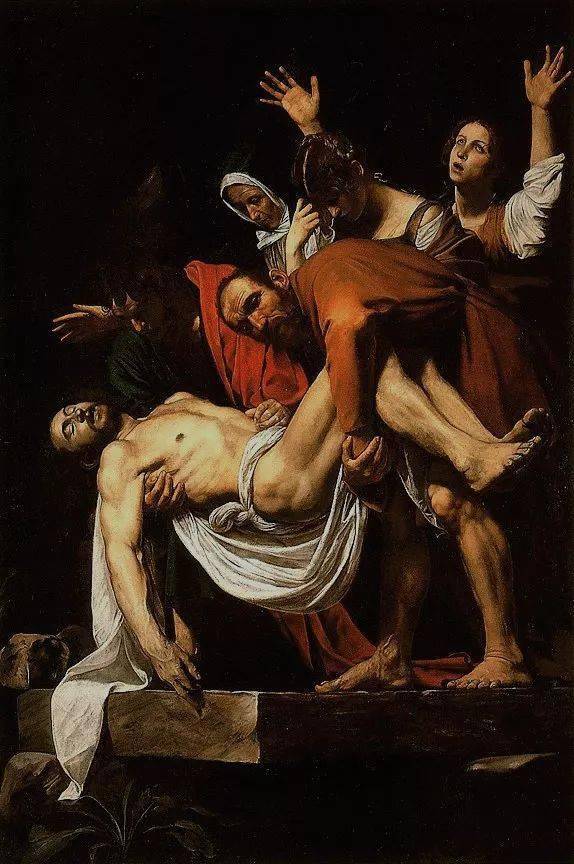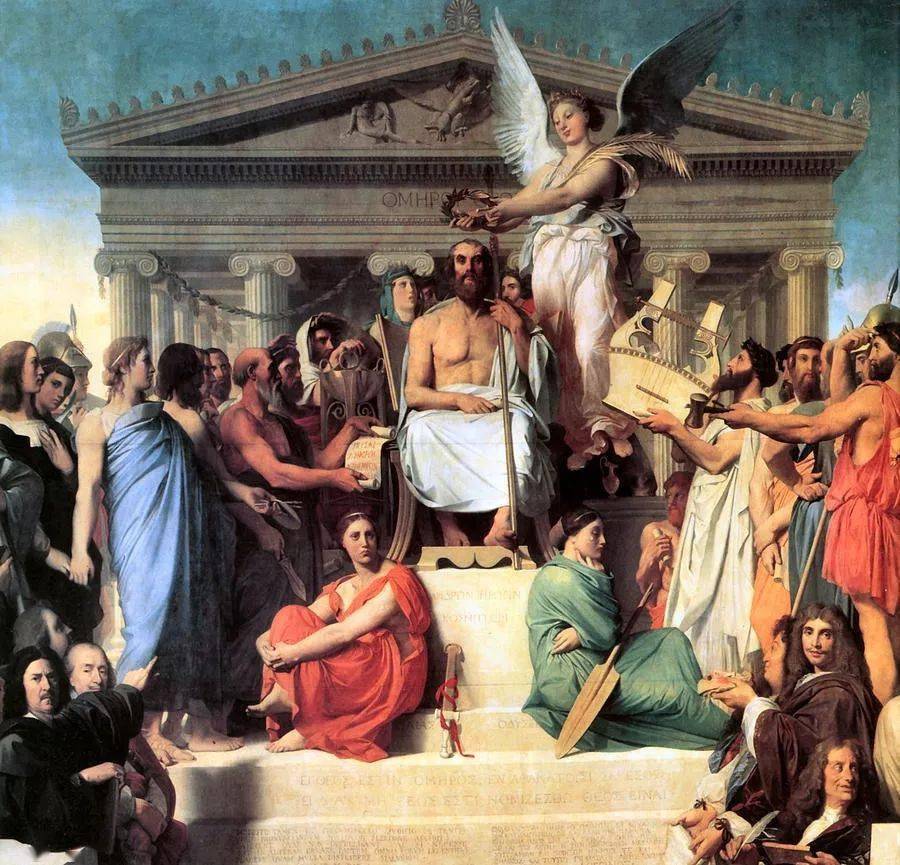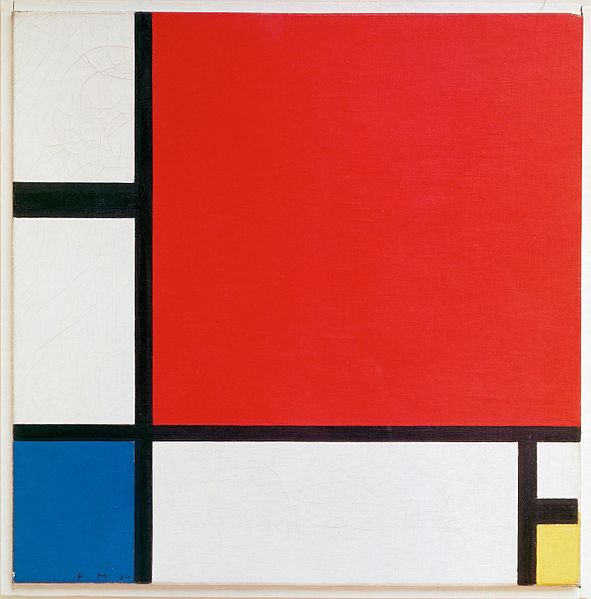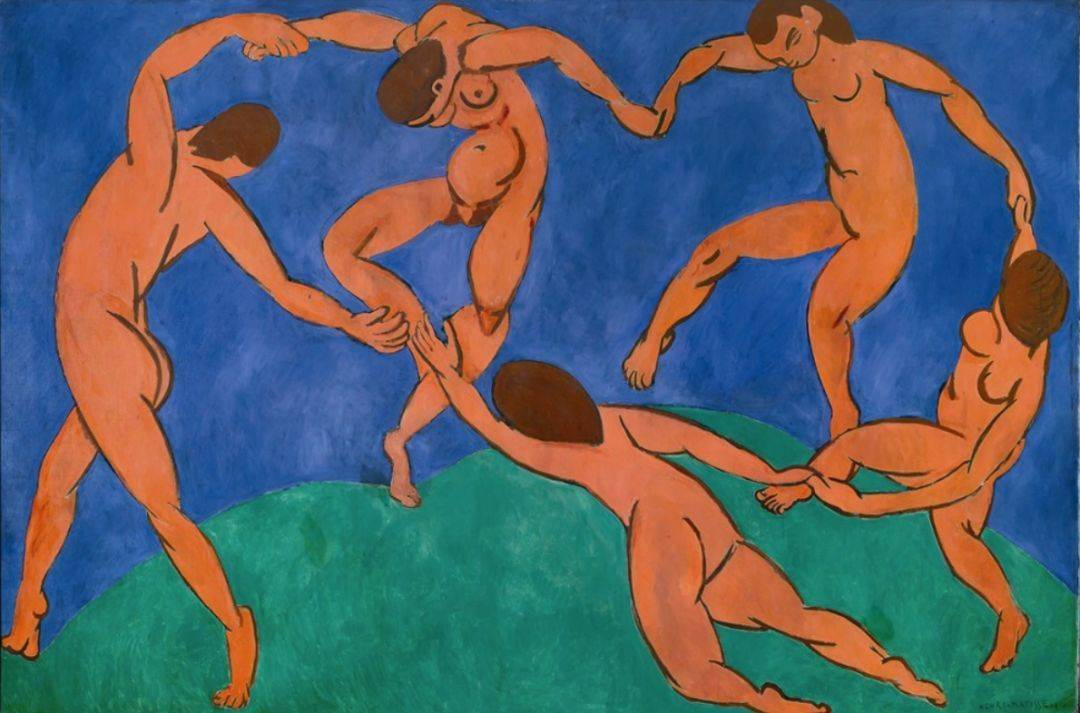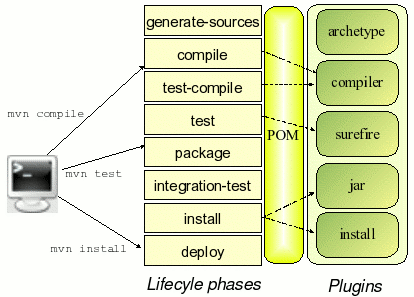MariaDB 调优相关
本文主要摘译自这里。 MySQL 曾经有独立的公司。但那间公司后来被 Sun 微系统公司获取了。 Sun 微系统公司又被 Oracle 获取了。原 MySQL 开发者担心 MySQL 成为闭源软件,因此成立了一家SkySQL 公司维护开源的 MySQL 分支–MariaDB。 MariaDB 支持的存储引擎包括: InnoDB/XtraDB 后者是前者的加强版,属于事务性存储引擎,也叫 ACID-compliant(ACID 遵从的)。XtraDB 是 Percona 开发的存储引擎,整体向下兼容。使用普通的 mysqldump 会耗尽 cpu(因为要把数据库转化成正经的 SQL 语句)。而 xtrabackup 在大库上的备份、还原、冗余都表现得更好(因为像 Oracle 一样是二进制备份吗?)。 TokuDB。另一个事务性存储引擎。以高压缩率著称(最高25倍压缩)。适合小空间存储大数据。 MyISAM。MySQL 上最古老的存储引擎。非事务性存储引擎,只支持表级锁,不支持 MVCC。 SphinxSE。非事务性存储引擎。这名字和古希腊猜谜语的怪兽,斯芬克斯一样。本以上是用...
KOA 初探
KOA 是 express 的进化版。都是被作者玩腻了扔掉的东西。 它简化了各个中间件层面的工作,提供了高级的“糖”,把各个中间件转化为了函数。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const Koa = require('koa');const app = new Koa();// x-response-timeapp.use(async (ctx, next) => { const start = Date.now(); // 到这里就停住了运行,让下一个中间件函数运行。 await next(); // 从下一个中间件函数那里返回 const ms = Date.now() - start; ctx.set('X-Response-Time', `${ms}ms`);});// loggerapp.use(async (ctx, next) => { ...
如何把 composer 锚定到 e2e 的复杂网络
下载并进入/blockchain-explorer 项目。 cd fabric-docker-compose-svt。 download_images.sh(不要让 start.sh 代劳,要用特定的版本)。 ./start.sh 建立这个隐藏文件夹 /Users/magicliang/.composer-credentials,如果里面有内容要先清空。 把公私钥导入这个文件夹,注意最后一个 keystore 的私钥可能会变化: 1composer identity import -p explorer -u PeerAdmin -c /Users/magicliang/Desktop/Programming/git/blockchain-explorer-cp/fabric-docker-compose-svt/crypto-config/peerOrganizations/org1.example.com/users/Admin@org1.example.com/msp/signcerts/Admin@org1.example.com-cert.pem -k /Users...
Cello 在 mac 上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opt/cello 和 /opt/cello2 以及下面的 mongo 和 fabric-1.0 都尽量把 owner 和 group 改成当前用户名和当前用户名组名。然后把这两个子文件夹用 docker file sharing 打开。 docker 会对 cello 下的 file sharing 有很麻烦的冲突影响。解决方法是建立一个 cello2 文件夹,然后在 cello 项目下用以下脚本把 fabric-1.0 的文件夹迁移过去: 1234#!/usr/bin/env bashARTIFACTS_DIR=/opt/cello2sudo cp -r ./src/agent/docker/_compose_files/fabric-1.0 ${ARTIFACTS_DIR}sudo chown -R ${USER}:${USERGROUP} ${ARTIFACTS_DIR} 然后修改 vi .//src/agent/docker/docker_swarm.py,把 COMPOSE_PRO...
以太坊相关研究资料
《以太坊的 gas 费率一览表》 《以太坊学习笔记:私有链搭建操作指南》 《以太坊中的账户、交易、Gas和区块Gas Limit》 StackOverflow 上的问答:以太坊主链到底需要多大空间? StackOverflow 上的问答:怎样提供无限次数的智能合约操作? 《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以太坊 (译文)》 《以太坊官方文档》 《以太坊私有链搭建指南》 《以太坊关于搭建私有网络的 wiki》 《预充值以太坊资金的方法》。注意看 carchrae 的回复,这里面也提供了拷贝私钥复用私钥的方法,可以考虑在多节点的情况下使用。 《一本与参数有关的介绍怎样搭建私链的 gitbook》。 StackOverflow 上的问答:以太坊的网络难度是否可以静态锁死?注意看它还有个相关的子问题。如果网络算力的稳定的话,应该不会出现难度增长才对。 值得大读特读的 geth 的文档。特别是挖矿、账户管理的部分。 geth 的命令行选项。注意,有些选项在当前版本中已经消失了,如(gpomin、gpomax)。 StackOverflow 上的问答:如何降低测试网络中的难度。感觉没多大用。 搜索以...
把 Unix 的 Domain Socket 转成可本地访问的 TCP 端口
使用管道命令的做法: 1socat -d TCP-LISTEN:2376,range=127.0.0.1/32,reuseaddr,fork UNIX:/var/run/docker.sock 简洁的做法(使用守护进程而不是使用管道命令) 1docker run -d -v /var/run/docker.sock:/var/run/docker.sock -p 127.0.0.1:2375:2375 bobrik/socat TCP-LISTEN:2375,fork UNIX-CONNECT:/var/run/docker.sock 从容器内往外看的主机,对应外部主机就是 127.0.0.1的端口 ping docker.for.mac.localhost 通常结果是192.168.65.1。 值得参考的文: http://brieflyx.me/2015/linux-tools/socat-introduction/
银翼杀手
2049没好人。
JVM 与编译优化
Java 的编译分期,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有些情况下还有额外的第三种编译过程): 编译前端(前端编译):把 *.java 变成 *.class 文件的过程。也就是把源语言文件变成中间语言文件的过程。典型的例子有:javac、Eclipse 的 ECJ 的工作过程。 编译后端(后端编译):由 JIT(Just In Time Compiler)把中间语言(字节码)转换成二进制目标体系结构机器码的过程。典型的例子有 HotSpot 的 C1、C2 编译器的工作过程。 AOT(Ahead Of Time)编译器直接把源代码编译成二进制目标体系结构机器码的过程。 早期(编译)优化 javac 自从 1.3 版本已经不再支持 -O 的优化了。所有的优化策略集中到后端编译里。这样没有经过 javac 编译的 JRuby、Jython 程序,也可以享受到 JVM 的优化福利。 javac的编译过程,大致上是: 解析和填充符号表(Parse and Enter)。 注解处理(Annotation Processing,Java 5以后加入的过程)。 分析与字节码生成(Analyze an...
基于栈的虚拟机
基于栈的虚拟机 全景导图 mindmap root((基于栈的虚拟机)) 核心架构 操作数栈 局部变量表 栈帧 执行机制 字节码指令 基于栈的运算 指令集简洁性 设计优势 可移植性 代码紧凑 实现简单 典型应用 JVM Python虚拟机 .NET CLR 模式总览 # 模式名称 一句话口诀 覆盖场景 1 栈式计算 数据流与控制流分离,操作数隐式传递 JVM字节码执行、表达式求值、递归调用 2 栈帧隔离 每个方法调用独立的执行上下文 方法调用、异常处理、线程隔离 3 指令紧凑 操作数位置编码在指令中,减少指令长度 字节码压缩、跨平台分发 问题定义 为什么选择基于栈的虚拟机架构,而非基于寄存器的架构?这种设计如何影响字节码的生成、执行效率以及跨平台可移植性? 核心概念 虚拟机架构分类 虚拟机按照指令集架构主要分为两类: 基于栈的虚拟机:指令不指定操作数的位置,操作数从栈顶弹出...
Hyperledger Fabric 网络的启动步骤
本文是截至日前(2017.10.27)时对官方教程和自我实验的重新梳理。 Hyperledger Fabric 可以说是 Hyperledger 的拳头项目。虽然同为 Apache 的顶级项目,但大部分其他项目都以 Fabric 为基础。它是顶级项目中的顶级项目,可以认为是0级项目。 docker 要有高于 17.06.2-ce 的版本。docker-compose 要有 1.14.0 及以上的版本。当然当前的高版本的 docker 已经自带了高版本的 docker-compose,这通常不用担心。 安装1.9+ 的 Golang。应该预期这样的结果: echo $GOPATH /Users/xxx/go 如果这个结果出不来,考虑当前 Shell 的环境变量没有正确设置: export GOPATH=$HOME/go export PATH=$PATH:$GOPATH/bin 要用一个很特别的 nodejs 版本。6.9以上,却不能用8.x。npm 也有特别的版本要求: npm install npm@3.10.10 -g 要用...